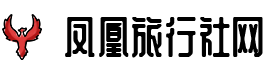邦达草原简介
概况:
茶马古道出左贡,经由以拥有众多美女而著称的田妥,穿出玉曲江河谷,一下子就迷失在茫无边际的邦达大草坝里。那是一片片苍茫起伏、雄浑辽阔的原野。藏民们将这片原野称为邦达。邦达大草原究竟有多大?到现在恐怕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它地跨五六个县,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人烟。据说,它大到连飞鸟都飞不出它的边际。马帮们只是把它叫做500里长草坝。那是一片让人心醉也让人有些恐惧的大草原,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夏天草原上到处是沼泽地,到处流淌着雪山的融水和雨水。高原上的雨不下则已,一下就是瓢泼盆倾,昏天黑地,有时还夹着冰雹。雪山融水和雨水慢慢又汇聚成无数的小溪,最终流到玉曲里,这景象在无垠的草原上恰似一条条飘飞的丝带。遥远的地平线尽头,是一座连一座山势平缓而又变幻无常的山岗。秋天从拉萨转回的时候,草坝常常为茫茫的大雪覆盖,无垠的原野上似乎了无生机,连到处都是的乌鸦都藏起了它们的身影。有时回首望去,在一片辽阔沉寂的白色旷野中,马帮商队仅只是一串小黑点,它们像一队蚂蚁一样缓缓移动,似乎在将比他们自身重得多的东西搬运回自己的家里去。那巨大的雪原形成了奇特的自然景观,更突显出马帮们敢于闯荡冒险的胆魄和毅力。在这诺大的草坝子里,,因为它地处滇藏、川藏道路的中段,所以有的商号在这设了点,派人住守,负责交接货物和找牦牛放短脚。现在有一座兵站和一个运输站建在路口上,离邦达乡有几里远。路口还有军人家属和四川人开设的小食店。那里的房屋全用铁皮作顶,房前屋后,扔满了啤酒瓶和生锈的军用罐头盒。草原上还有些游牧的牧民,一家一顶牦牛毛毡帐,零零星星散布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见有人路过,老远他们就挥手喊叫,也没什么事情,只是他们太寂寞了。他们拴在帐篷前的藏獒更是一阵咆哮。在由邦达至昌都方向三、四十公里处,原野显得更加宽坦。60年代印度对华战争中,解放军在这儿抢修了一座军用机场,有十几位军人为此献出了生命。1993年我经过这里时,天正下雨,我围着他们的纪念碑转了一圈。经多年高原风霜雨雪和阳光的剥蚀,这碑已显得很古老,古老得像一个失传的神话。它站在那儿,看着机场那无尽头的跑道,看着连绵无垠的湿漉漉的荒原,那跑道亮亮地裸露在原野上,感觉怪怪的。当时,邦达机场正在扩建。军人、民工和车辆以及爆破声将这沉寂了多年的荒原搞得轰轰烈烈的。后来,在报纸上看到邦达机场通航了,那是件了不起的事。邦达机场的海拔要比拉萨机场高许多。我想它大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机场,不知它的运输情况怎样。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跋涉的马帮大概无法想象在那荒原上会有一座现代化的机常尽管有了机场,邦达原野仍苍凉荒芜,即使在夏日的夜晚,那里的气温也好像能将骨髓都冻成冰。黑云死死盖在草原上,雾汽蒸腾,阴风惨惨的。远天处不时掣两道闪电,竟渺小得可怜。当年在这荒原上,唯一的热气就是马帮呼出的。过去入藏道路到邦达就分成了三路,一路到昌都、类乌齐、那曲,马帮习惯上称之为大北路。由林芝又可以向北到工布江达,或向南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经加查、泽当、贡嘎、曲水到拉萨。1923年,法国著名藏学家、探险家达薇·尼尔以55岁的年纪,,就是从云南境内踏上这条路,最终进入了拉萨。甚至,有一条路直接从玉曲河谷里的扎玉,不再北上邦达草原,而是向西经由藏南的然乌、波密,直达工布江达和拉萨。这当然是行程最短的直线。但是据说这条路万分艰险,马帮根本无法通行,所以也就没人敢走。但民间肯定有人在走这条路,据达薇·尼尔在她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的描述,在他们进入帕隆藏布峡谷后,遇上了许多朝圣者,这些朝圣者有的就是从藏南走的,他们只要翻越伯舒拉岭就能到然乌、波密。赵应仙也记得,波密的麝香是最好的。帕隆藏布两岸有着亘古至今的原始森林。这条路格外艰险,沿途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当时很少有人敢走这条线,马帮就几乎没有走这条线的。现在的川藏南线就从这一线通过,不过每年都会被泥石流冲得个乱七八糟,无法通行。也正因为它的艰险,所以那一带的风光景色十分壮丽,用人间仙景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1989年我从那条路走过时,为那从未见过的美景震惊无比。帕隆藏布两旁的大山完全为原始森林覆盖,江水油黑油黑的,好像凝固了一样,无声无息地,那沉而酷的暗流阴森吓人。森林中有的是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树下的灌木丛阴冷潮湿,潜伏着不知多少蛇类,你仿佛能听到它们伸吐着舌头的声息。不时有一些漂亮得令人心醉的鸟儿从水面上掠过,它们的鸣叫才是真正的天籁。第三路就由邦达直接西去,那就是长而辽阔的邦达草原(马帮们叫“长草坝”或500里“长岗子”),它一直延伸过郭庆,直到海拔4800米的莫波拉山口下。那海拔高度当然是我后来查出来的,据说那山口并不很难走,身体棒的赶马人还能在那山口上像猴子一样蹦跳呢。由四川入藏的马帮,从康定出来,经理塘、巴塘,过惹不得的察雅(藏区的人普遍认为察雅人粗犷蛮野),或从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然后到昌都(旧称“察木多”),他们大多也不走大北线,而是抵达瓦合寨或恩达,与滇藏路合为一线,从嘉玉桥过怒江,西去洛隆宗、边坝、嘉黎和工布江达,最后到拉萨。这是传统的官道。到了邦达长草坝,人烟日渐稀少,除了几顶黑黢黢的牧民的帐篷,马帮常常面对的是渺无人烟的荒野,燃料也只有靠沿途拣拾牛粪。那时西藏的荒野里动物野兽很多,邦达草原更是如此。在茫茫草原上,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它们长着长长的尖尖的黑色犄角,马帮带着的狗一见它们就兴奋得不行,吠叫着就是一阵狂撵,受惊的羚羊就跳跃着从马帮中穿过逃走,速度快得惊人,狗根本追不上。半个世纪后我多次从那一带走过,根本不见藏羚羊的影子。他们大概被猎杀得差不多了。藏北还幸存着一定数量的藏羚羊,忽然在西方世界时兴穿藏羚羊绒做的衣服,藏羚羊绒的价格一下子比黄金还贵,于是藏羚羊就遭殃了,它们遭到了残酷的猎杀,尽管它们早已成为国家保护动物。所以说,人才是地球上最凶残的动物,他们无休无止的贪婪需求,导致了许多生物的灭绝和地球生态的急剧恶化。除了可怕的狼之外,邦达还有熊、豹子这样的猛兽。在一些静谧的夜晚,马帮们能听到惊天动地的吼叫,有经验的人就知道,那是老虎在哪儿饱餐了一顿大肉,到河边来饮水发出的叫声。马帮们虽然都带着枪,但他们都知道那不一定管用。像熊、豹这样的猛兽要是一枪打不死,它们就会不顾一切扑上来拼命,那就不得了啦。据说即使它们当时无法拼命,事后它们也会牢牢记住攻击它们的仇人,然后再伺机报复。野兽有野兽的法则。可怜的是那些骡马,它们一闻到豹子或老熊的气味就会吓得直发抖。所以,马帮们从来都不轻易向那些猛兽,尽管他们经常见得到豹子和熊。有几次赵应仙还见过老虎。但有一点,只要不逗惹这些猛兽,它们一般也不主动来惹马帮。但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例外。在走西藏草地那些年头里,赵应仙手下有一个奔子栏的藏族马脚子,叫什么名字赵应仙已经想不起来。那就是一个倒霉的家伙。他辛辛苦苦在茶马古道上赶马,他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有自己的骡子。这使我想起了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的故事。他的命运也跟骆驼祥子差不多。他是个特别得力能干的马脚子,每次都能赶12匹骡马,因为他表现出色,老板东家特意奖给了他一匹骡子。这可让这位马脚子高兴坏了,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骡子,尽管只是一匹,但有了第一匹就会有第二匹,有一天他也许就会成为自己的马帮的马锅头。赵应仙带着这个马脚子,他带着属于自己的骡子,又一次踏上雪山草地。滇藏一线的马帮都有这样的规矩:你帮大商号赶马帮,也可以将东家给自己的骡子放到马帮里一起走,草料都在马帮里一起开销。如果驮的是东家的货物,就可以得一份运费,如果驮上你自己出资置办的货物,那赚得的钱全归你自己所有;马脚子同时也要赶其它的马,挣一份工钱。这是商号老板对赶马人的照顾。这些老板自己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用他们的话说,自己要找钱,也要让别人找钱。茶马古道上的商人和马锅头们一般都有这样的气度。但这位有了自己骡子的马脚子并没有从此走运。一天他们走到邦达上去一点一个叫“斗子里”的地方,照例扎营开亮,马脚子们照例在睡前打了一阵乱枪,以吓跑那些野兽。然而那天夜里出了怪事:一头豹子闯到了马帮的营地,声息全无就咬死了一匹骡子,而那匹骡子偏偏就是那位马脚子独一无二的那一匹。在四、五十匹骡马里,那头该死的豹子只选择了那个马脚子的那匹该死的骡子,只能说该那个马脚子倒霉了。对那匹骡子来说倒不见得是倒霉,也许还是一种解脱,──从遥遥无尽的艰苦劳役之中得到了解脱。那匹骡子被咬断了喉咙丢在那里,豹子并未下口大吃。那倒不是因为它肚子不饿,而是豹子喜欢吃臭肉,要等死骡子臭了它才转回来饱餐一顿。第二天早上看到自己骡子的尸体,那位马脚子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就像祥子的车被大兵抢走了一样。那时一匹好骡子值百十块半开银元,那位马脚子辛苦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才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骡子,结果却被豹子就这么咬死了。这大概就是命吧?后来那位马脚子只有将自己的货物分给别人帮驮,还得继续走他的马帮之路。他后来又有没有自己的骡子,赵应仙也就无法知道了。过去在茶马古道上,见个豹子什么的已是经常的事,老熊就更是多。它们一般也不敢来惹马帮,因为马帮都带有枪,而且晚上开亮都要烧一堆篝火,在睡前还要打上几抢。但是营地里不能放有生肉,也不能杀什么生,否则那些猛兽闻到一点儿腥味儿就会不顾一切闯了来。据说在滇南丛林中行走的马帮还有一种绝招,睡前在篝火里撒一把草果、八角,任何野兽就不敢接近了。除了野兽,那时草地里还有野牦牛和野马。在荒芜的草原里,它们曾一度是那里的主人。那里就有像大野牛沟、大野马滩这样的地名。现在,除了一些藏羚羊、黄羊和藏马鸡,野牦牛和野马几乎都绝迹了。在西藏的神山上,打猎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汉人、纳西人的马帮不在此列,他们管不着。西藏的野物可多了,雪鸡、白鹇、岩羊、兔子、旱獭什么的都有,赵应仙他们可以偷偷去打,不让藏族知道。打来可以改善一顿伙食。藏族因为信仰佛教,不随便杀生,所以就没有打猎一说。他们自己要是偷偷打杀了什么动物,那就是非常不得了的事,土司、头人或活佛会严厉惩罚他们。他们即使见到个小土司、,连头都不能抬的。那制度是很残酷的。而云南的马锅头就可以跟这些土司头人平起平坐。他们所带的东西也可以随便乱放,天气热了,就将楚巴脱下,放在路边用一块石头压上,都没有人会动。哪怕是很值钱的东西,像驮子什么的,都可以随便放着,没有人会动它们的。在那片神奇的高原上,马帮们不仅目睹了西藏社会的种种残酷制度,也目睹了广大藏民的善良美好和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幸,还见识了许许多多奇特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值得一提的是,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上路以后,就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了。到了邦达这样的地方,就只有荒草了。西藏大部分地区又高又冷,没法种蔬菜,藏族也没有种菜的习惯。再说,大多数时日都是在杳无人烟的地方行走,到哪儿去找蔬菜?赵应仙他们当年曾从丽江带过一些白菜、萝卜、南瓜籽去,在扎玉种过。我们50年后去时,在玉曲江沿途的村寨里都吃到了蔬菜,有白菜、南瓜、土豆,甚至还有青椒,不知是不是要归功于马帮?不过在赵应仙他们走西藏草地时,茶马古道上有的是野菜。从云南一路进入西藏,到处都有各种野菜。赶马人有时边走边采,到晚上开梢时,就有美味可口的野菜吃了。如果天天顿顿就是酥油茶、糌粑,对平时很讲究吃蔬菜的丽江人来说就有些难以接受了。幸亏有那些野菜。它们为赶马人提供了大量维生素,也提供了难得的佳肴。在到邦达之前的那些大山和河谷里,到处是野葱、野韭菜,比家栽的细一些,骡马都可以放开吃。野菜里最为美味的,可能要算鲜嫩的竹叶菜了,苦凉苦凉的,又有一股清甜的味道,采了来煮腊肉,最好吃了。因为它长得像嫩竹,故名。这东西要在海拔高的多水的林间空地里才生长。高原上还有一种野果叫夏巴拉,是一种带刺的灌木,果实很多,像些小灯笼一样挂满了枝头,熟了的果实就是一颗红红的小灯笼。不过它没多大吃头,只皮底下有一点点肉,然后就是跟果子差不多一样大的核。那年我们走在路上,饥渴时就采来装满衣袋,然后一把一把不停地吃,多少也能吃到点内容。熟透了的夏巴拉就红得发紫,很甜,肉也沙沙的,面面的。沿途野桃子也多,不过一个个又小又硬,根本不能吃。夏天过去时,草地、林间也少不了各种蘑菇。赵应仙他们当然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那都是马帮们相互传授的。有现在很吃香很昂贵的松茸,有一窝菌等等。他们常吃的一种是白白的,嫩嫩的,因为丽江没有,就叫不上名字,只把它叫白菌。它的味道最好。在田妥过去一点点的地方,在怒江边一个叫牟门的地方,那里居然出产葡萄,甜的葡萄,有食指头那么大,很好吃。赵应仙住在邦达的时候,曾经到过那里采买那儿藏族自己酿造的葡萄酒,买了来过年喝。那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村子。那里还出产一种最好最体面的毛料,叫“牟门拉瓦”。拉瓦就是毛料布的意思,完全用手工纺织成,最好了,在丽江都很出名,丽江人去哪儿做客带上一点“牟门拉瓦”作礼物,就不得了啦。给人家做坎肩什么的最好了,纳西女人最喜欢了。那毛料细细的,跟现在的细毛呢一样,“他们会搞呢,不得了呢。”多年后赵老先生还赞不绝口。那时牟门的好多人家都做那“牟门拉瓦”,一般都是妇女搞。牟门的毛料好,与当地的羊有关。他们的羊毛最好了,羊绒长长的,比棉花都细,妇女从早到晚都拿个纺锤纺线,然后再织成布,最后还自己染色,染得最多的藏族最喜欢的紫色。。赵应仙他们打猎最常打到的猎物还有雪鸡,学名叫藏马鸡,现在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它们通常二、三十只一群群地活动,白天一起觅食,晚上栖息在一起,但有一只有经验的老鸡不睡,担负着为鸡群放哨警戒的任务,一有动静,它就会发出警报。雪鸡很笨,既飞不高,又飞不远,长的又漂亮惹眼,味道又十分鲜美,自然就成了人们猎获的对象。别的狩猎对象还有白鹇,个子有点大,嘎嘎地叫,但是肉有点酸。另外还有兔子、獐子什么的。有时候打不到什么野味,赶马人就挖开旱獭洞,于是往往能发现里面屯积着数量让人吃惊的草籽和一种叫延寿果的植物根茎。延寿果比花生米小一点,也像花生一样长在地下,其实是一种植物的草根,一节一节的,紫红色,有的长长的,是茶马道上最好吃的野果,而且名字也非常好。在草原上经常可以见到它们,人就可以扒来吃。如果将它拌上酥油,放点糖就更好吃了。德钦人最爱吃这种野果。马帮偶尔带一点回丽江,大家也很爱吃,是馈赠亲朋好友的又一种珍贵礼物。无论是进西藏,还是从西藏回来,马帮们的行囊里从来不会缺乏各种稀罕古怪的物品,他们将各种各地没有的东西带来带去,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各种各样的交流。赵应仙在茶马古道上就见到一种奇异的现象:西藏有一种鸟会跟老鼠住在同一个窝里,相互之间还很有义气。在天冷的时候,鸟儿会背着小老鼠去晒太阳,没吃的时候,老鼠就会把扒来的延寿果,与鸟一起分享。我现在仍然认为赵老先生是我见过的最为诚实的人,在他跟我讲述的马帮的故事里,我从未发现他掺了水分。他不是那种想象力丰富的人,更不是那种乱编胡吹的家伙。有时我还有些抱怨他的讲述太实在太干巴太缺乏文采了。但听了这个鸟鼠同穴,陆空动物会师的故事,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但老人向我保证那是他亲眼所见,绝非天方夜谭,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都知道这事。我当然没见过。我只能说,在那片高原上,也许什么都是可能的,什么奇异的自然现象都可能存在,就像那儿存在着许多奇异的文化现象一样。事实上,跟人一样,动物为了求生存,就不得不改变生活的习性以适应环境。在那茫茫大草原上,连一根树枝都没有,鸟儿们到哪儿做巢?而它们又不会打洞,它们只得下地入鼠穴借作雀巢了。至于它们是如何征得老鼠的同意,并能相安无事而且相互友爱帮助,只有待动物学家去研究了。